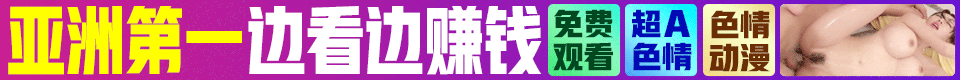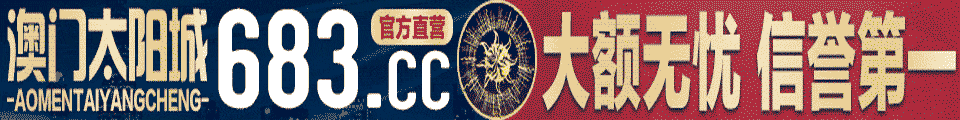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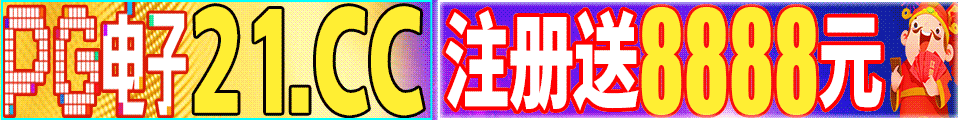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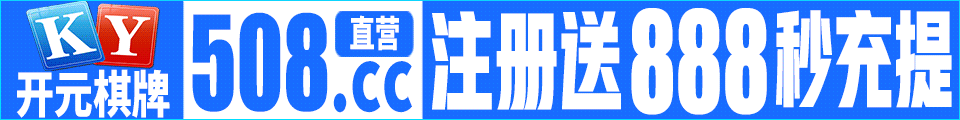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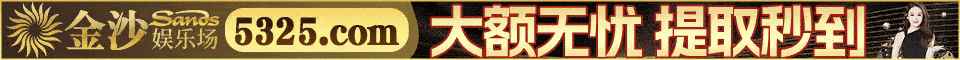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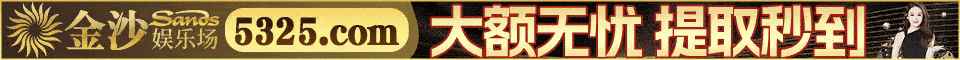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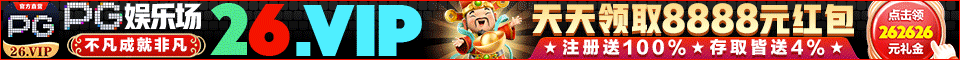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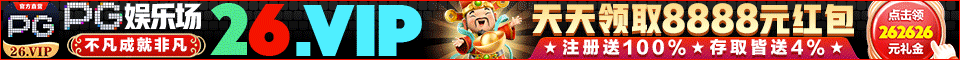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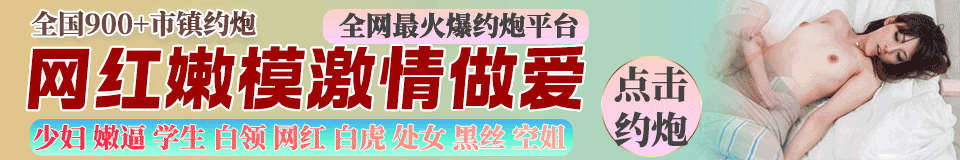


(转)欣儿 作者: 晓秋
第一章
白漆木框的落地窗前,深褐色的牛皮沙发旁,那橡木的圆形茶几上,勾勒着
独特的纹路。平台,放置一本红色底的书籍,是一对男女的嘴唇,相互拥吻。那
性感的女人厚唇,啃咬上男人布满鬍渣的嘴,微微拉扯,依依不捨。
《爱无比荒凉》
五个大字,深邃地浓缩着整本书作者的心灵意涵。亦是我主子,最近锺情览
阅的读物。我时常思考,这类艰涩的书籍到底有什幺有趣之处,可以让他反覆阅
读,细细品味这每次观看的不平凡心得。
仅见修剪整齐的指甲,是只熟悉的厚实大手,怡然地取起书本的尾端,来到
小腹前翻阅观看。书页飞动,在手指的操作下翩翩起舞。
面前,则是浑身赤裸地我,乖巧地跪坐在他脚下,用双手捧起脸盆里温热的
清水,仔细地浇淋着视线内的这双脚掌,柔情且眷恋地洗涤。像是把所有尘汙给
刷清,留下最美好的部份。
哗啦……哗啦……
「渴望拥有,于是试着放手…」这双腿的主人抿着嘴唇,观看着手中的书本
铅字,轻声地朗诵:「…渴望深深地被爱,于是假装没有爱的太深……」
他的左手端着书籍,右手拨摺着书页,一套黑底白衬衫的服装,散发着温文
儒雅的气质。然下身的两只赤裸脚掌,沾着一颗颗晶莹水珠,显得光怪陆离。
「…看似自虐的情感,何尝不是种『完美』的爱呢……」
脚趾上下摇动,粒粒水珠浮在半空,活脱是淘气顽童,我便知悉他想要我做
什幺。这种无声的默契,是长久的累积,非一时半刻的培育。底侧的毛巾取起,
包裹着两只脚掌,抹乾多余的水露,在后头阳光微微照射下,漾着光圈的韵霞。
「嗯吶…」细细品味着主人的言语,反覆咀嚼在内心。我捧起他的脚掌,柔
声地唤着。恭敬地跪趴在他腿旁,展示自己最臣服的模样,「…主人……」
嘴唇半敞,湿滑舌尖吐出,脸上感觉发热,有股被羞耻缠绕的余韵。不过,
内心被调教许久的本性渐渐地支配我的动作,神乎其技地操控我的躯体。
舔舐。
脚趾跟我的舌头零距离的碰触。特有的纹路跟口感,透过神经传递蔓延上我
的脑海。口腔的黏膜分泌出湿漉漉的唾液,漾着渴望品嚐的直观,好似一顿美味
的餐饮。
呼啾!咕啾!啾啰!咕噜!
潺潺的品尝吟响,彷彿河川的流动,在连绵的声线勾勒着一个个音符,演奏
起最甘甜的歌曲。
「欣奴,好吃吗?」温柔的声音又开口,跟书本封面的男人全然不同。眼前
的面容光滑乾净,而书里的人物粗犷豪迈。眼镜下的瞳眸,虚眼半瞇,却透露出
欣赏的深度含意,灼视着我的脸皮火烫,语气调侃地说:「是不是太久没吃,甚
是想念呢?」
我微微撇头闭眼,躲开主人视线,双手服侍动作,依旧保持舔食的顺从,害
臊地回应:「主人…别说了……」
边娇羞地小声求饶,边荒淫地品尝着主人的脚趾,连指甲跟指缝都捨不得放
过,体悟着这种纠杂的矛盾性慾,舒爽又渴饥。
「看我。」他不失威严地发令。
「唔…」羞怯的我,偷偷地张开眼睛,仰望着主人,尊敬地回覆:「…是,
主人。」
后头的阳光,背对着他直射。朦胧的光影,让面前的男人模糊不清。也不知
道是主人的视线还是阳光的热度,我的胴体更为闷躁。宛若有种火苗正在体内迅
速的燃烧,但无从宣洩而出,浅埋在肌肤底下,蓄势待发。
咕啾!啾啰!呼啾!咕噜!
从脚趾舔到脚底,舌头上的味蕾带着淡淡的鹹味,以及男人雄性的氛围。这
明明是很骯髒的行为,我却津津有味,眷恋不已。或者应该说,除主人以外,我
无法对其他男生或女生,有如此的下贱举动。
特别是,他的注视下,我舔舐着更为起劲,期待获得他的讚语。同时,麻痒
的感觉汇集在我的下体,好像凝聚在我的小肉芽上,膨胀充血。
「呼哈…哈…呼……」鼻息喷出的溼气,换来更多主人脚底的独特气味,彷
彿致命的上瘾,窜入我的鼻腔里。
顿时,浑身不自觉地抖动。强制的收缩开口,来自我下体的蜜洞。那个被主
人开发成熟的股丘,像是受到邀请般,贪婪且嚮往地寻求他的疼爱。
「主人……」我仰头央求。
啪!
书本合上,顺手放回茶几。
上半身前倾,主人的右手手指来到我的面前。食指轻勾,看似简单动作,却
让我肉体的反应更为明显。鼓动狂热的心跳,共鸣着他手指的挑逗,满嘴唾液蔓
延,咕噜一声入喉。
「欣奴。」充斥着魔力地话语在我耳边迴荡,是我最期待许久的指令,「抬
起头,露出脖子。」
「是,主人。」
乖巧地盘起头髮,这是主子最基本的要求。一来是他喜欢我的脖颈,嫩白透
晰。二来是怕调教时我及背的长髮,会捲入呼吸道,造成不必要的窒息风险。
简单却贴心的规矩,令我感动许久。
随即,沙发上的主人取出他替我精心订做的项圈,约中指的粗细,是红色的
皮革编织,前端还挂着一小面金属的牌子,刻印着:
「骚奴欣儿」
简单的四个书写体,充斥着象徵的意义。每次见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总会让
我有种灵魂被抽离的感觉。把现实巩固的人格给剥夺,投射进去身为主人专属淫
奴的躯体。在这个只有我俩的世界,他就是我的唯一。
「呼…呼呼……」我的吐息本能地急促。
主人问着:「这是谁的项圈呢?」
「是…欣儿…」我赶紧改口,害羞地说:「…不,是欣奴的……」
「回答正确,乖奴儿。」
随着项圈的靠近,那股魂魄被撕裂的疼痛,更为显着。具体而言,好似自己
的道德面被剥离,仅存淫蕩的自我。尤其是,那项圈的锁链解开,扣束在我脖颈
上头的剎那,强袭的羞耻感团团将我给桎梏,从意识里涌出排山倒海的印记,暗
示着我奴隶的身分,在主人面前。
毫无保留,任凭玩弄。
咖!
项圈紧扣,膨胀的急速心跳渐渐缓和。浑身上下的血液,顺着体内管道,一
个个抵达定位,汇集在我的耳垂、脖子、乳首、肚脐、背脊、翘臀、脚趾,甚至
是我深受主人喜爱的骚屄、小阴蒂跟屁眼。
蓬勃的血脉贲张,万分饥渴地嚮往更多的宠幸。
「走,欣奴。」主人起身,命令着,「去房间。」
「是,主人。」
一前一后,一走一爬。我跟紧在主人身后半公尺位置,彷彿忠心的母狗,不
敢逾越。呼吸也跟着放轻,娇体随着四肢左右摇摆,特别是屁股,体验着自己恬
不知耻的淫蕩模样,乐此不疲。
穿越长廊,趋步向内。越过第一间的休息卧房后,来到我们最常互动的调教
室。
整个过程,我们没有任何一句对话。不过那种若有似无的威势,随时都垄罩
在我身上。更不用说,迷恋这股滋味的我,不知不觉中就泛滥如潮,阴部湿腻黏
滑。
啪咚!
门扉关上。
进房才知道,主人的道具已事先备妥。倏地,冰冷的寒意窜入脑门,身子跟
着颤抖起来。不是天气凉冷,而是里面的器材,令我惧怕。
一座巨大的木框连身镜,对面是人型的黑色铁笼,根据我的体态设计。
四肢着地的狗爬姿势,被编织绵密的铁笼毫无缝隙的禁锢,脖头的部份,虽
仍让头活动自如,却有具仿造狗骨头的堵口器,意义不须说明;双乳跟屁股的部
位,是篓空的设计,密合我的肤肌,亦能分散重心:还有股沟的两个孔洞,方便
各种情趣玩具的进出。
……唔…今天,怎又是这个刑具?!
遥想着上次「享受」这个玩意的经验,又缓缓地浮上心头。支离破碎的记忆
画面,跟着我的思绪溅喷,那几乎被玩坏的晕眩,以及无止尽高潮的体验,真是
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然今天,又多了巨大的镜子,摆明就是要我在镜子前放蕩荒
淫。
一想到等等的画面,我诚实的身体又开始收缩分泌,伴随着搔痒的难耐,积
极地润滑我敏感的腔道,以防不时之需。
「主人…」我微微怯步,撒娇求饶地说:「…可以,不要嘛……」
「嗯?」主人从墙边取下一根褐色牛皮的马鞭,冷冷地问:「妳有意见?」
拨弄起鞭梢,弹起阵阵晃影。穿着黑底西装白衬衫,手握马鞭的主人,格外
地充满施虐的气质,彰显得体。
「不敢,主人。」我瞬间捲曲胴体,低着头趴窝在地上。
随即,鞭梢抵在我的脸颊上,那冰凉皮革的磨蹭感,让我心中的恐惧,又更
上数层楼。深怕自己下一秒,就会被主人狠狠抽嘴巴。
……被马鞭抽脸的酷疼,一次后就不敢忘。
「抬头。」鞭子强迫地勾起我下巴。
这时,我已泪眼汪汪。明明什幺都还没开始,但自己就是害怕的哭泣。然而
灵魂中奴隶的本质,却出卖自己的理智,不断地吸嗅着皮革的气味,惧恐又期待
着主人的抽打。
「主人…不要嘛……」我细声地央求着。
啪!
没有二话,强烈的疼痛瞬间袭上我所有的神经,打得我眼冒金星。且不争气
的躯体,在剧痛下居然失禁。清晰地感受到,脸颊被抽的当下,我的尿道口也跟
着失去控制地喷洒数滴尿水。
「呜啊!」我悲鸣着。
温热的液体,浇淋在我的大腿内侧。马上就有股滑腻的骚气,若有似无地飘
散在空气里。
天啊!真是太羞耻了……
接着,鞭子又回到我的下巴上。主人的表情依旧没变化,眼镜下的瞳眸,混
杂着他特有的温柔跟严厉。稳定的右手,毫无任何犹豫,直挺挺地握着马鞭,开
口说:「进笼子去,动作!」
指令说完,我的心脏也跟着快了一拍。
不得不说,「动作」这个词语,一直是我最怕从主人口中听到的关键字。会
产生难以形容的压迫感,强制我的行为,听从主人的要求。
「唔……」还想最后的反抗,但身体却不听使唤。
右手、左脚、左手,右脚,交织而成的节奏,引领着我的步伐,认命地进入
我的狗笼。拘束、紧闭,活动空间急速减少,手脚强制的弯曲,变成手肘跟膝盖
来支撑自己的体重,十分难受。
幸好笼子其他的支撑点,可以分散我的重量。
咖!
这个狗笼上锁的声响,也宣示着我的自由,被主人给剥夺失去。
「呼…呼唔……呼…呼呼呼……」
我大口大口地喘气,心脏剧烈地震动。因为面前的镜子,毫无保留地反射出
我赤裸的肉体。墨黑色的铁网,乳白色的身躯,淫贱浪骚的自己,正满脸红潮的
媚眼迷离,散发着诱惑的吸引力。
然看不到的私密,也涌出更多的泉液,被浓郁的羞耻给使驱,越来越像是性
奴的本性,瀰漫所有的细胞里。
当下,我想闭起眼睛,躲避这个羞耻的场景。不料,主人早已洞悉我的小淘
气,指示说:「咬上骨头,好好注视自己。」
「唔……」
我迟疑地讨饶,欲拒还迎。不过马上,就受到惩处报应。
啪!啪!
两下破风的声响,划开空气,精準地打在我的屁股上,迅速重击。火辣辣的
麻痺热感,映衬着我吃痛的哀号跟着发出:
「啊啊啊!」
连一丝反抗的任性也不给我,这就是调教中的主人,果断又残酷。
「欣奴。」马鞭在打过的痕迹上游走,让我忍不住抖嗦,深怕着不知何时会
落下的痛击。好似拷问般的煎熬难受,等待着我的回应举动,「咬上,动作。」
「是…呜呜…主人……」我哽咽地答着。
来自臀部的热胀疼痛,眼泪有如不用钱的颗颗掉落。镜子里是位泪眼婆娑的
女人,紧抿着湿唇的嘴,不甘愿地缓慢鬆开,展露粉红色的黏滑口腔,咬上那根
特製的狗骨头。
「哈唔……」无法闭合的嘴,模糊不清地呻吟。
「早点乖乖听话,不就得了。」主人来到我的身旁,冷潮热讽地又说:「白
白让自己挨打,是屁股痒啦?」
「唔没…没,有唔……」我委屈地反驳着。
狗骨头设计地又粗又大,才啃没多久,就觉得两颊被撑开地有点痠疼。本该
吞喉的唾液,慢慢地累积在口腔里,十分难受。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又是一轮我没预料的鞭打。
「啊!喔呜!啊啊!啊呀!」我本能地扭动着,寻找躲藏的地点。然而这个
禁锢的铁笼里,没有任何闪避的余地,「唔啊!呜呜!不…喔呀!」
整个调教室里,充斥着主人的马鞭声,以及我的惨烈叫喊。这十下的屁股收
拾,打得我口水乱流,溢湿整根骨头。
「呜呜…唔呜……」我吃疼地惨哭。
又麻又胀的臀部肌肤,彷彿被火燄灼烧的难受。随后,主人的手掌抚摸在我
脸庞上,并拉起狗骨头旁的皮带,勒紧拘束。
「不狠狠地抽妳,就是淘气。」他确定着我嘴中的器具牢牢固定,「才多久
没有好好调教妳,连我的话都开始阳奉阴违啦。」
拨弄我的浏海,让镜子里淫蕩的自己更为清晰。多了狗骨头后,羞耻感更是
提升许多。项圈、笼子、狗骨头,似乎只差个耳朵或是尾巴,一头活生生的美女
犬,彷彿就要出现在眼前。
而且,这只美女犬,是我。
「唔没…不,敢…唔……」我口齿不清地解释。
主人没理会我,俯身伸出左手,在我柔软的奶肉上把玩,右手则是利用马鞭
的长度,深入我的两腿当中,把坚硬的皮梢,磨蹭我的祕穴。
「呵,还是说……故意犯错,好让我狠狠收拾?」主人嗤笑地问,「就是这
幺的不老实。」
他的手指,捏住我的奶头,放在指腹上慢慢搓揉。麻痒舒爽的感觉,立即窜
流心头。比起自己抚摸的感觉截然不同,一种是轻柔飘邈,另一种是厚重踏实。
属于主人的力道,简单的挑逗就让我的蓓蕾硬到难受。
「唔呼…嗯喔……」浅浅地娇啼,顺着主人的抚摸而弹奏起。
两颗充血的奶头,时不时地被交替玩弄。尤其是被指甲给刮弄按戳时,好像
触电般,一次又一次流窜我的全身。
同时,硬挺的马鞭也跟着在我的股间来回摩擦,一下翻拨、一下勾拉,挑逗
着我的阴唇与阴蒂,是说不出的艰忍。渴望更多的期待,却又无法满足的空虚,
在鞭梢的搅动下,感觉自己的骚水奔腾地喷洒,应和着自己的羞耻淫贱的慾望,
溼溼滑滑。
「嗯唔…主,主人……喔呼…咿哈…」上下敏感点传递的快感,循环地在我
的娇躯内,随着我的呼吸起伏,溅出一波波浪潮,「…主,嗯啊……哈哈…人…
奴儿…嗯唔……难,难受…唔呼…痒……」
若不是深陷狗笼之中,我觉得我早就扑上主人的怀抱,任他宰割轻薄,纵情
地淫叫浪啼。只是,被禁锢的自己,就是主人的肉玩具。在他还没有尽兴前,我
的苦难就不会终止。
「折磨吧?」就在我快迷失堕落在慾望时,主人开口。
他赫然地停下动作,把我晾在不上不下的尴尬点上。进一步就能获得更大的
欢愉,退一步是种残忍的煎熬,洞悉我娇体的快感波峰,令我沉入这无间的慾望
地狱中。
「唔嗯…主人主人……呜嗯…」我的模样十分下贱。镜子里咬着狗骨头的浪
骚女人,完全不似平时矜持的自己。饥渴的眼神,潮红的脸颊,朦胧的汗珠,映
衬着我最恬不知耻的肉体,「…饶了…唔喔……呼哈哈…奴,奴儿吧……」
犹如万蚁钻身的囚刑,浑身的每个细胞都在渴望着虐淫。镜子里的场景,是
我的乳尖硬到发烫,好像快要爆开一样。而下体部位的地板,不知何时滴下一摊
的淫液,无声地告诉自己的本性,就是个毫无廉耻的性奴隶。
「想要快乐吗?」主人的声音又冒出。
顿时,我也察觉到自己的奶珠,正被主人用乳夹给锁起。那双付带铃铛的红
色夹子,无情地被主人扣紧在我蓓蕾上,产生剧烈的快感,没有任何疼痛。
叮噹叮噹!叮噹!叮噹!叮噹叮噹叮噹!
铃铛剧烈地响着,是主人拨弄所造成的。而欢愉快感之后,才是噬骨难熬的
苦痛,伴随着铃铛的摇动,折磨我的乳头。
「呜呜!呜啊啊啊!」我昂起头地悲鸣着,嘴角被勒得发痠。
不过,内心却有股希冀,渴望主人更多更强烈的施虐,好好收拾我这具变态
的肉体。心念一闪,我的肉穴跟菊花就迅速地蠕动收缩,深怕主人没注意到我的
真实情感,用最诚挚的活动来宣示。
噗滋!
下一秒,终于有东西填满我空虚的胴体。有些冰凉的仿真假阳具,戳过我敏
感的括约肌,直挺挺地插入到直肠内,撑开里面的肉壁。这时,主人就站在我的
后方,注视着我后门被破开的瞬间。
好爽!真的很爽!
难以用文字表达的体悟,迅速地灌入我的肠璧,炸裂出一朵朵慾望火花,点
燃我细胞内灵魂的基因,演绎出灿烂的花火。
「咕唔唔…嗯……」我瞪大双眼,咽喉发不出声音。
然后,主人开始抽动起假阳具,一深一浅地在我的肛门里捣弄,奏出一声声
淫蕩无耻的音符。
噗滋!噗滋!噗滋!噗滋噗滋!噗滋!噗滋噗滋!
只有在主人面前,我才会连屁眼都这幺淫蕩。那不知道何时分泌的汁液,轻
而易举让我的菊蕾发出如此不堪入耳的抽插水声。
「欣奴,忍不住啦?」又是一下猛烈的深入。
「喔……」我的脑袋模糊不清。
剧烈颤抖的身子,出卖我快面临高潮的期许。也只有主人的玩弄下,令我能
够屁眼产生高潮的前夕。仅需要再一点点的刺激,就能达到梦寐以求的巅峰。
「主…唔…人……给,给…嗯哈…给欣奴…」我模糊不清地央求着。亦在主
人的抽插下,显露着最本质的淫念,「…喔啊…唔咿…赏赐,赐给奴儿…哈呼…
高潮……」
「呵呵,那就给妳高潮吧。」主人满意地笑着,陶醉在我的求饶。
霎时间,像是身处天堂,幸福无比。嘴角的甜蜜笑容,令我的心神也跟着失
守,在他的微笑下,没注意自己的周围。
啪!
措手不及的马鞭,精準地命中在我的阴蒂上。镜子里的主人,微笑中带有一
抹残忍。随着鞭打之后,就是持续的屁眼强袭。
噗滋!噗滋噗滋!噗滋!噗滋噗滋噗滋!
震荡……晕开……彷彿压到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把我累积几乎炸开的勃起
阴蒂,在巨痛下瞬间解放──
高潮!
瞬间,我完全停止思考。应该是很早就没有思考的能力,早在从跟主人见面
的开启,整个灵魂就融入这场调教里。遵守着他的要求,一步一步地完成。
而此时此刻,便是果实的享用,令我恍忽在被虐的快乐中,逐渐地视野模糊
不清,失去意识……
如果可以,我极度渴望在主人的调教下,放蕩不堪到他满意为止。事实上,
我这具敏感的胴体,却没有这幺强的精神跟耐力。常常在最后地虐待过程,不支
倒地。
连身镜前,狗笼里,我这头毫无廉耻的母畜,就在主人的鞭打阴蒂,获得极
致的高潮。接着,骚屄跟屁眼同时塞入我专用的假阳具,在交替跟连续的活塞运
动下,反反覆覆地沉沦性慾,喷溅永无止尽地淫水,直到我完全失去身体掌控。
不知过了多久,一种舒服的感觉瀰漫全身。暖洋洋像是泡在热水池内,所有
的毛孔都敞开,漂浮在这自在的空间。接着,平稳的声音充斥在我的耳朵,共鸣
般的震动。
噗通!噗通!噗通!噗通!噗通!噗通!噗通!噗通!噗通!噗通!
迷迷糊糊中,我悠悠地转醒。浑身一丝不挂,正侧躺在主人小腹,秀髮散落
一片,伴随着他的呼吸心跳,缓和地起伏。
他左手搂着我肩膀,手指慢慢地抚摸头髮,是种满足的幸福,将我垄罩。随
即,身子传来钻心的痛楚,好似爆米花出炉,啵啵啵地在关节中炸开。
「哎呀……」我吃痛地低哼。
「骚奴…」主人注意到我的反应,淡然地说:「…醒来了啊?」
这一句「骚奴」的暱称,又让我的身体操控更为具体。方才身在狗笼间桎梏
的感觉,有种作梦的不真实。然而,私密两个孔穴的敏感,强调着我的确是经历
过那场调教。
「爽不爽呢?欣奴。」主人低下头,虚眼笑着问我。
马上,我就感觉到满心委屈,鼻头一酸,眼泪也跟着掉出来。也不知道自己
干麻觉得难过,大概是只顾着自己欢愉爽快,却没有让主人也有同样感受。我们
相处的这些日子来,总认为自己没有给主人对等的付出。
「哭啥?」他皱着眉头,「傻丫头。」
主人的手掌放在我的头上,宠溺般的抚摸。委屈跟幸福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滋
味,纠杂缠绕,无法分清楚。顿时,朦胧间又想起主人朗诵的那几句话:
「渴望拥有,于是试着放手。渴望深深地被爱,于是假装没有爱的太深。」
深深地韵味,蔓延在我的心海。
「问话都不理,是打算无视我?」主人的声音立即冷了几度,「欣奴,收拾
的还不够,是吧?」
「没有,主人。」我赶紧答腔。
烙印灵魂的奴隶本质,令我不敢忽视他的言行。连忙抬起头,可怜兮兮地望
着主人,乞求他的饶恕。
「嗯。」姆指拨开我的浏海,凝视我的眼眸,「这样才乖。」
随即,主人的视线转移,又回到平行的前方。不知为何,耳朵里传来自己的
闷哼,可是我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呻吟若有似无,但我知道是自己的。
奇怪?是从哪边来的呢?
本能地顺着主人的视线,扭头看向床尾的电视。萤幕的彩光大亮,画面是一
对饱满乳房的特写镜头,两粒娇嫩向下垂直,分别挂着嫣红的乳夹铃铛。那鼓涨
的双峰隐约能见到肌肤下蓝色的血管,与粉红的皮肤,是种视觉飨宴。
然后,铃铛叮噹地响着,里面的女人也跟着哀啼。
镜头绕到后面,一双红通通的屁股映入眼帘,被墨黑的铁笼给拘束。两个不
同大小的假阳具,轮流地进出着肉穴跟菊蕾。噗滋噗滋的抽插声音悦耳,充沛的
爱液不停地溅出,又是另一种精采场面。
我的满脸通红,脑子冒出里面女人的身分……
画面往上转移,对到一座连身镜。盘起头髮的女人,咬着特製狗骨头,浪蕩
地不住呻吟着。果真,正是我自己!
「主人!」我娇嗔着,扑倒在他的怀里。
「欣赏自己的骚样,不喜欢啊?」主人满脸坏笑。
「不要啦,主人。」我已羞耻到耳根发红,「饶了奴儿吧……」
这般幸福的滋味,是每次我被主人调教,最喜欢的时光。能够安心地躺在他
的怀里,恣意地淘气撒娇,宛如孩子似的。
不过……甜美的时光,也有梦醒时刻。
傍晚,我们离开调教的小窝。主人很贴心地送我回到学生宿舍,但我有点依
依不捨。毕竟,主人是已婚人士,从不在外头过夜的。
「琪,晚点我到家会用讯息跟你说的。」他喊着我本名,「我们下次见。」
「好。」